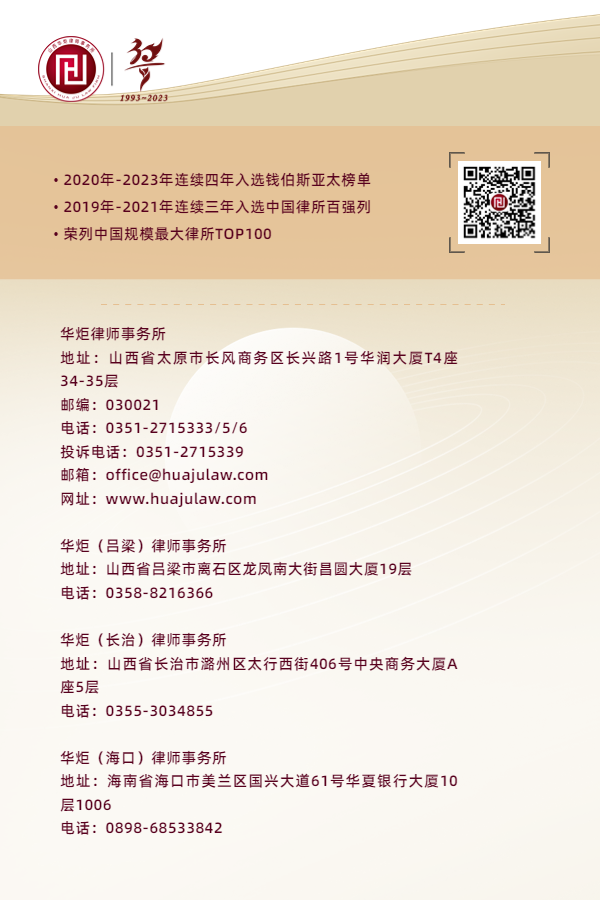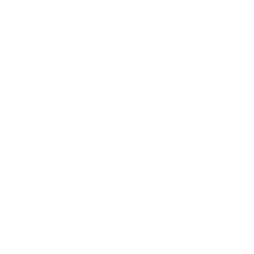法悟 | 帮信?还是掩隐?
2024-01-10


一、基本案情
2021年2月,被告人魏某甲在从事“网络兼职”时进入某专门洗钱的微信群聊,之后为谋求好处向张某乙出卖多张银行卡,提供其本人名下8张银行卡帮助进行支付结算,将转至自己名下银行卡内的资金转至本人微信账户,再将该资金通过微信转账至他人账户。2021年3月4日至3月19日,电信诈骗被害人王某、徐某、包某某、蒋某、余某、李某等人被诈骗钱款共计人民币106409元,该资金被转入魏某甲名下的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民生银行等账户,之后魏某某将以上钱款转至其微信账户后再转到他人指定账户内,协助进行资金转移,银行流水共计145万余元。
二、主要争议
1.魏某甲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该观点认为,魏某甲所从事的“网络兼职”本身就是以洗钱活动为内容,其对他人实施的上游犯罪显然处于明知状态。在明知他人正在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时通过出售银行卡为其提供支付结算的行为符合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帮助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2.魏某甲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该观点认为,虽然魏某甲的行为可以被认定为是:明知是赃款而通过在银行卡和微信账户之间进行转账的方式改变赃款性质的行为,但这并不表明其就是符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恰恰相反,既然魏某甲所从事的“网络兼职”本身已经具有了“洗钱”的目的和性质,那么就已经表明其行为是在上游犯罪完成后才实施与介入的,而非上游犯罪实施过程中。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司法解释以及《关于深入推进“断卡”行动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的内容,对魏某甲应当按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进行定罪处罚。
三、为什么要对两罪进行区分
如果说关于罪名的区分是为实现定罪的准确性并精准揭示行为罪质与罪状的话,那么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不同罪名所造就的刑罚差异可能是其更为关注的问题。毕竟,相比定罪而言,具体的刑罚种类与期限才是决定其能否真诚接受刑罚后果并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直接性与实体性因素。而从掩隐罪和帮信罪的法定刑来看,二者确实存在着罪名严重程度与刑罚期限的差异。详言之,帮信罪不仅在法定刑上因最高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明显低于掩隐罪的7年最高法定刑,而且其在入罪标准上也有所不同。例如,以支付结算、转账等帮助为例,支付结算型帮信的情节严重标准为支付结算20万元以上,但掩隐罪的成立只需要在数额上达到3000元至10000元以上,情节严重的第二档法定刑也仅仅要求在数额上达到10万元。显然,相比帮信罪而言,掩隐是一个典型的重罪。此种情况下,如若对行为的定性不准确,那么便会造成罪刑不均的情况,并最终有损司法正义。
四、如何对二者进行区分
(一)根据行为的时间节点进行区分
从时间节点上对帮信罪和掩隐罪进行区分,可以被认为是最核心与最根本的界定方法。原因就在于,根据帮信罪的罪状规定,行为人在实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行为时正处于整个犯罪的过程之中,被帮助的正犯行为以及最终的犯罪结果都还没有完全实现,其仅仅是帮助正犯完成犯罪的一种辅助性手段。但掩隐罪则明显不同。根据掩隐罪的内容规定,掩隐行为本身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与犯罪所得收益的犯罪,既然该罪以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为前提,那么就意味着上游犯罪实际上已经完成并既遂。可见,行为人的帮助行为是处于犯罪过程之中还是犯罪完成之后,能够成为两罪区分的决定性因素。这不仅能够正确揭示两罪的罪质,也能够符合共犯的基本原理。
(二)根据行为的具体对象进行区分
帮信罪和掩隐罪在行为对象上的差别不仅是两罪的重要区分点,而且也能够成为认定上游犯罪是否完成(也即整个犯罪是否仍然处于犯罪过程中)的标志性要素。正如前面所说,帮信罪行为人所实施的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行为,而掩隐罪所掩盖的是上游犯罪人的犯罪所得或其犯罪所得收益。一个面向正犯行为,一个面向赃款赃物,二者可谓是完全不同。关键在于,如何对事中行为和事后行为进行划分。以我在前面所举的案例为例,魏某甲通过银行卡、微信转账所涉及的款项,到底是上游犯罪已经完成后的赃款赃物,还是认为上游犯罪还未完成?在我看来,既然对于电信网络诈骗之类的财产犯罪来说应当以犯罪人的财物取得作为既遂要素,那么当犯罪人尚未实现自身对犯罪对象(财产)的控制时,就不能认为这些财产内容已经转化为赃款赃物,而是应当认为其仍然是正处于犯罪过程中的犯罪对象。因而,只要上游犯罪行为人尚未实际控制这些财产,就不能以掩隐罪来进行处理。
(三)根据主观明知的内容进行区分
实践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案例,有些人经济困难,在网上有人说能办理出大额的信用卡,然后就把自己的卡给了对方,说是用于粉饰流水,结果被用来走钱,然后被定罪;有的人确实不冤枉,但有的人也确实是被骗,但是都被定罪了。本人认为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实际上,从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出发,客观行为与结果只是认定行为构成犯罪的基本前提,至于行为人构成何罪,行为人的主观要素认定同样甚至更为重要。如若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其主观认知是帮助他人完成信息网络犯罪活动,那么自然应当以上游犯罪的共犯或帮信罪来处理;如若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其主观上认为仅仅是一种包庇、销赃、掩饰隐瞒上游犯罪人赃款赃物的行为,那么自然应当以掩隐来进行认定。当然,这些主观认定的要素也是根据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来认定的。而且,这并也不违背《“断卡”纪要》第5条关于“行为人向他人出租、出售信用卡后,在的情况下,又代为转账、套现、取现等,或者为配合他人转账、套现、取现而提供刷脸等验证服务的,可以掩隐罪论处。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仅向他人出租、出售信用卡,未实施其他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标准的,可以帮信罪论处”的规定。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观点认为只有出租、出售信用卡而无其他实质性行为的情形应认定为帮信罪,而对于既有出租、出售信用卡又有代为转账等行为的情形应认定为掩隐罪。本人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原因就在于,同时存在租售信用卡和配合转账、套现并不表明行为人对该款项的犯罪所得性质具有明知,如若其认为帮助的是行为而非帮助隐瞒赃款,那么以掩隐罪来论处也不合适,这同《断卡纪要》中要求掩隐罪成立要满足“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要求也是一致的。
在帮信罪和掩隐罪的司法适用中,只是对两者进行区分尚不足以涵盖其中的全部问题,而且需要注意罪名适用的谦抑性。毕竟,帮信罪等罪名的泛化适用已然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根据相关资料,帮信罪依然是排名前三的一个犯罪,每年因此受刑的人在十多万。对此,本人认为应当充分激活《刑法》第13条但书的功能,如若行为人的罪量和作用力等可以满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要求,那么便应当对其予以入罪考量的限缩。
作者简介
张飞虎 律师
2011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供职于某基层法院,民事庭工作四年,刑事庭工作六年,曾担任刑事庭副庭长。2021年7月入职华炬律师事务所,现任山西华炬(长治)律师事务所投融资法律事务部主任。实战经验丰富,先后审理了各类民刑事案件500余件。理论知识扎实,先后发表多篇理论文章。
刑事犯罪辩护联系方式:18834561199
*本微信文章仅为交流目的
不代表华炬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