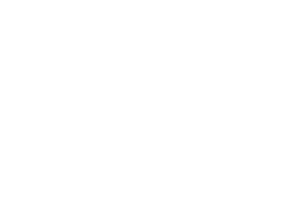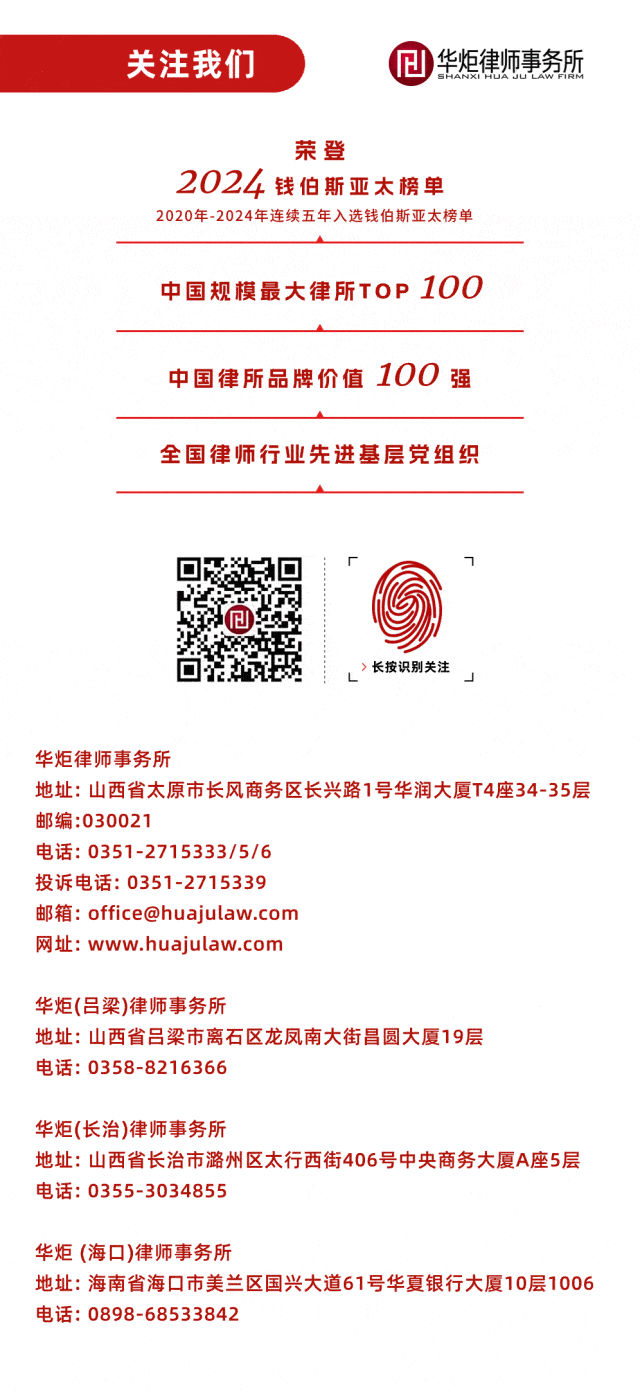华炬文萃 | 古代判词撷趣
2024-10-12


古代判词撷趣
HUAJU WENCUI
自周朝断狱听讼以来,判词即应时而生,它们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典籍中,犹如一粒粒珍珠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它们是法律文献的文学之花 。判词始于西周,兴于唐朝,成熟于北宋,至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古代文人的公堂判词一般都比较墨守成规,但也有许多判词写的才藻华丽、文采飞扬,引经据典、辛辣讥讽、妙趣横生。例如郑板桥的“僧尼私恋案”的判词:“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桃。从今入定风归寂,此后敲门月影遥。鸟性悦时空即色,莲花落处静偏娇。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就写得文采斐然、字字珠玑。笔者现就将古代关于大家所写的几篇有趣的判词挑选出来,以飨诸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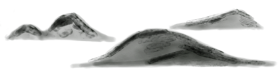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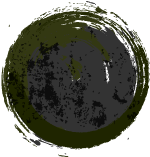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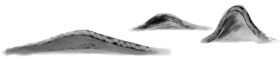
唐代诗人元稹,是新乐府运动的创造者,他的诗与白居易齐名,史称“元白”,元稹在朝为官期间,所作的判词文字优美,见之如沐春风、令人忘俗。一次,乙姑在田中种树,老邻长斥责其妨害谷物生长,乙姑不服告至元稹处,元稹判词为“百草丽地,在物虽佳,五稼用天,于人尤急。乙姑勤树市,颇害农收。列植有昧于环庐,播穑虽妨于终亩。虽椅桐梓漆,或备梓人之材;而黍稷稻粱,宜先后稷之穑。苟亏冒陇,焉用成蹊?纵有念于息阴,岂可侔于望岁?植之场圃,合奉周官;置在田畴,殊乖汉制。既难偿责,无或顺非。”元稹判词的大致意思是,“种类繁多的草木生长在肥沃的土地上,对于世间万物来说总是好事,但庄稼的成长却完全依附于农时,对于人而言更是着急的事情,民以食为天吗?你虽然在田间勤奋的种树,但对农作物的收成却是有害的呀。在田地中种树这种做法本来就违背了在茅庐周围种树的道理,田地中的树木虽然是柔韧之材,或许可以成为木匠的有用之物;但谷物的成长收成却是我们最先考虑的事情。如果庄稼长势不好,人连肚子都填不饱,纵使种上成排成排的树又有何用?树木即使长的再茂密葳蕤、蓊蓊郁郁,又怎么能同盼望谷物丰收的心情同日而语呢?将树木种在场圃符合常理,而要将树木种在田地,却是有违礼制的。既然你难以承担赔偿之责,那就不要做这些不对的事情了。”何等的样人才能写出这等富有诗情画意的判词,这本来就是一起再普通不过的田地种植树木的纠纷,可我们的元大人却引经据典,写得用语典雅洗练、论理酣畅,字斟句琢,扬葩振藻。
清朝康熙年间的名吏陆稼书在任时因以德化民,待之如家人父子,以至于达到“无讼”的最高境界,辖下也政清人和,庭可生草。通过其所写的判词可以窥见一斑。有一表兄汤寅因羡慕表妹慧芬美丽聪慧,欲以求婚,却遭拒绝,便四处散布谣言,谓其表妹如何不贞、如何失节,表妹投缳未果,遂哭诉至陆公处,陆公大怒,判汤寅杖一百,徙十年。陆公判词义愤填膺,开门见山首先说道“审得朱慧芬控表兄汤寅毁人名节一案,本县直为眦裂。女子以贞操为人生第一事,贞操保持,则乡里钦佩,族党景仰,否则即不齿于人类。朱惠芬端庄稳重,言笑不苟,正一四德兼全之女子。”随后又抨击汤寅“且正利用其备尝痛苦,以快一时之泄愤。而受之者辩即不可,忍又不能,大有求死不得、求生不得之恨。谁无女儿?谁无妻妹?易地以处,将之如何?天道果有知,汤寅其不得免乎?应从重治罪。”最后又劝朱慧芬道“惠芬二八之年华,待字闺中,才貌如此,而又加以贞白自爱,正不患有郎似玉。…曾参杀人,不疑盗嫂,天下固多此冤抑者。然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清浊之分,不在外而在内。鼓钟于宵,声闻于外。惠芬亦曾绝读诗书者,当必不以次而介介也。”一代名吏的手笔就是不一样,谆谆教导,苦口婆心,文笔娴熟,直抒胸臆。陆公判词中一面大肆抨击训斥汤寅,一面又极力安慰朱慧芬,名吏如此,辖下焉能不政通人和,风清气正。
袁枚是清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县令。他历任溧水、沭阳、江浦、江宁知县,“纾国更纾民,终为百姓福”,凡“吏民百事,有小讼狱立判无稽留”。他为人正直,率性坦诚,因厌恶官场,40岁即辞官隐退,离任时,百姓夹道相送,攀车饯酒。为官一方,此公不惧权贵,嫉恶如仇,处事办案颇受人称赞。一日有周、姚两位乡绅争地,袁县令经过一番核实,查清“一谓周姓祖产,一谓姚姓私产。既无官契,又无界石,穷搜旧案,遍诘邻人,亦均无可指实。盖已荒废五十年矣。”袁枚查清后认为周姓乡绅说是祖产,没有官方契约佐证,姚姓乡绅说是私产,可也没有房屋遗留的界石痕迹,查遍以前的档案,又遍寻附近的邻人,都不能证实,因为这房子已经荒废五十年了。正值县里当时修建育婴堂,苦无地址,袁大人为民做主,判道“本案争地,既不能断归周姓,又不能断归姚姓,曷若捐之公家,以成好事?谁无子女,谁非人子?育婴保赤,虽曰官吏之职责,地方人士亦应量力玉成,以助其事。况该地本非周姚两姓所应得,归入公家,何施不可?着即息争,毋再多渎。后日育婴堂告成,即以此判刊入碑志,作周姚两姓捐赠之地,以垂不朽。庶法与情两得其平。至今万里长城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两造亦俱可释然矣。此判。”周姚两位,你们不要争了,这块地既不能给你老周,也不能给你老姚,你们作为乡里的知名人士,不如把这块地捐献出来,修建育婴堂;育婴堂修成,立碑铭志时将你二人名字镌刻上去,岂不名垂千古?
袁枚还有一篇判词,也挺有趣,说的是袁登礼之子少礼娶妻贾氏,不想贾氏娇养,未尽中馈(妻室)职责,袁翁以荆木鞭笞儿媳,儿媳哭诉公堂。袁枚感觉到荒唐可笑,判词中遂训斥袁翁“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小妮子年幼无知,教导不妨稍肃,而鞭笞朴责,非翁姑之所应有。冠子不言,发子不笞。子尚不可,何况乎媳?是本县不能不为袁登礼告诫者也。”而后又教育袁少礼“妻者,齐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举案有相庄之雅,送有如宾之敬。夫夫妇妇,而后家道以正。纵有百恶,岂无一善?是本县又为袁少礼训责着也。”接着劝慰贾氏道“夫唱妇随,妇本从人。翁姑即是父母,更当孝敬。不宜稍存芥蒂,有碍服老奉养。日为人妇,转瞬即为人母。今之所以伺翁姑者,亦即他日之所以使子妇。此本县更为贾氏勖勉者也。”最后,袁枚判道“应即归家,毋再起衅。父慈子孝,夫顺妇从。和气致祥,共守勿渝。”两篇判词显示出袁枚面对诉讼,并不是呆板四平八稳的训斥,多是耐心的劝导和说教,用语精炼、贴切,而且也可以看到其尊重女性、以礼释案的特点。他的语言铿锵有力,神完气足,真挚情感流露无疑,又岂不感人至深,被当时的官吏争相效?
李鸿章是清朝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影像资料中的李中堂往往是严肃呆板的大人形象,但在读他的“禁宰耕牛之批”判词中也有其可爱、至情至性的一面,试看“动物之中,惟牛最灵,亦惟牛为最苦。佐民耕稼,则犁雨锄云;努力挽输,则任重致远。彼既有功于万家,人胡忍心于一割?肉飞血洒,惨目伤心;就戮而哀鸣,鼓刀而堕泪。观其觳,深可悯怜矣。夫百务皆可资生,何必操刀为活;五味尽能适口,奚难舍此一脔?既据禀请,重申禁令,特再遍行申饬。倘有视为具文,教而不改,本部院姜柱不移,有言必信。一经告发,立置重典。勿谓忍心射利,三尺可漏也。”判词流水行云,而且用情至深、深情并茂,读后焉能不令人动容,再行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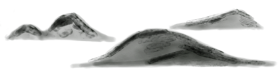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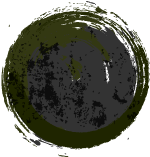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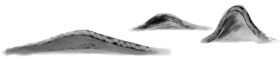
古代的判词,写的严谨细致、情法交融,而且判者多博学多才,判词中大量引用经诗名句以及杂记小说之言,对事实、理由进行叙述论说,措词贴切,文笔直抒胸臆,使人看后感觉到心悦诚服,醍醐灌顶。面对当今判决书的现状,我们应该仔细的借鉴古代判词的优点,扬长避短,文书中不妨也引用些弘扬传统美德的名言绝句,使文书在呆板生硬的法律基础之上,增添些温暖柔和的道德亲情。
文 | 白雁军


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业务委员会主任、争议解决法律事务部主任、山西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山西青年法律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山西省律师协会诉讼与仲裁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法学会港澳台理事会常务理事、山西省电视台、广播电台特约嘉宾、山西省调解学院外聘高级专家、太原市城南公证处法律专家
*本微信文章仅为交流目的
不代表华炬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